<strike id="mewo0"></strike>
<ul id="mewo0"></ul>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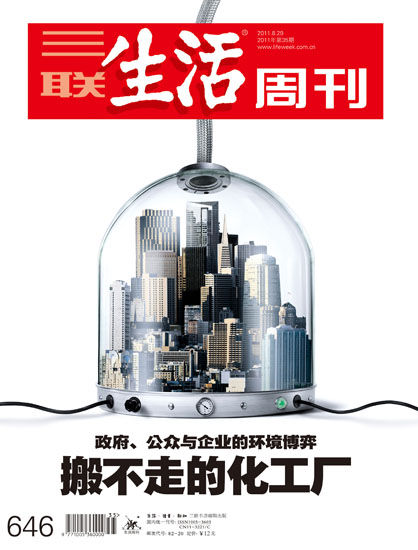 三聯生活周刊201135期封面
三聯生活周刊201135期封面
 大孤山石化區是大連重要的石化基地
大孤山石化區是大連重要的石化基地
 2010年9月17日,浙江金華市區秋濱街道一廢棄廠區內發生廢酸泄漏事件,泄漏強酸約8噸,刺鼻的氣味在周邊彌漫
2010年9月17日,浙江金華市區秋濱街道一廢棄廠區內發生廢酸泄漏事件,泄漏強酸約8噸,刺鼻的氣味在周邊彌漫
 綠色和平自身項目主任賴蕓在排污口取水樣
綠色和平自身項目主任賴蕓在排污口取水樣
政府、公眾與企業的環境博弈
搬不走的化工廠
主筆◎李偉?? 攝影◎于楚眾
8月14日,大連市政府宣布大連福佳大化PX項目立即停產并搬遷。這個占地80公頃的化工項目,含流動資金共投資95億元,是目前中國單系列規模最大的芳烴項目。
大連市民也許得到了一個滿意的結果。但問題在于,這樣一個從工程立項到環境測評都一路綠燈的重大項目,為何在投產26個月后遇到了如此強大的阻力和反對?一個近百億元的項目的巨大損失該如何承擔?它將如何搬遷,搬到哪里?這并非是一個單純技術就能回答的問題。因為,福佳能夠搬離大連,但龐大的化工業卻無法從中國撤退——2000年后,中國進入了新一輪的重化工業時期。化工業的增長始終維持著GDP增速的兩倍。2010年我國石化業總產值為8.88萬億元,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,其中化學工業產值居世界第一位。預計到2015年石化產業的產值會達到15萬億元左右。
現實的情況是,化工業是我國國民經濟支柱之一,其重要地位無須贅言。我國已生產和上市銷售的化學物質大約有4.5萬種,其中列入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危險化學品名錄的有3000多種。從某種意義上講,這4萬多種化學物質構成了我們身邊的世界。
問題是:每一座城市、城市中的居民該如何與化工業共處?換一個角度也許更貼切——化工業如何與公眾保持和諧而不是對立?如果有了這個前提,福佳大化的百億元損失是否就可以免于浪費,畢竟這是一筆巨大的社會財富。在重大項目的實施過程中,企業、政府、公眾構成了參與的主體,也是博弈體系的主要力量。企業代表資本與技術,是項目的投資方;政府擁有行政力量,是監管者;而公眾則是環境問題的承擔者,也是利益最相關群體。
但在目前的博弈格局中,企業成為主導力量,決定了項目進程。政府是項目的利益受惠者,因為投資會帶來GDP、稅收與就業。作為利益最相關者的公眾,卻處于弱勢地位,不僅參與度低,意見也無法得到尊重。這種博弈并不平衡。
2003年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》開始實施。2006年《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》明確要求:“對涉及公眾環境權益的發展規劃和建設項目,要通過聽證會、論證會或社會公示等形式,聽取公眾意見,強化社會監督。”國家環保總局《環評公眾參與暫行辦法》特別指出:公眾參與是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重要途徑,而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是公眾參與環境事務的前提。
但在項目決策與運行中,公眾缺乏參與的狀況并未有本質的改觀。“環境影響評價法”雖然規定了公眾參與的原則,卻并未給出公眾參與的明確途徑和程序,在方式方法上也語焉不詳,甚至對政府如何對待公眾意見也沒有規定。更重要的是,公眾意見對環評審批并不擁有否決權。這導致公眾缺乏對重大項目設計和可行性研究的參與權和監督權,甚至連最基本的獲得環境信息和參與環保事務的知情權也付之闕如。畢竟,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是公眾參與環境事務的前提。
沒有公眾對于“環評”的反復質疑和挑剔,那么該如何保證“環評報告”的質量?該如何相信它是經得起推敲和考驗的?如果公眾將利益委托給專家,這些受雇于企業和政府的技術派們是值得信任的嗎?“科學主義”并不能代替公眾知情權與參與權。
這就導致在項目完工后,公眾與企業之間始終處于對立狀態。公眾以抗議的方式表達對環境的不滿,當事故發生后則陷入恐慌。而企業往往更愿意通過繳納罰款或搬遷完成“救贖”。當環境事件爆發時,政府則陷入被動狀態。沖突—調解—罰款—搬遷—繼續沖突,但環境問題依舊沒有解決。
在我們的時代,公民自身的環境意識已前所未有地提高,與公眾參與制度的落后形成了鮮明反差,這也帶來了制度革新的壓力。解決環境與發展的問題,需要維系一個企業、政府與公眾平衡博弈的格局,共同參與,相互制約。
如果重大工程的決策始終以效率為目標,而忽視規則的平衡,那么,效率也終將付出不該付出的代價。■
誰來制約化工業?
企業、政府與公眾構成了三方博弈體系,如果其中公眾力量過于弱小,則會使這場博弈處于失衡的狀態。資本沒有了對手,化工業就會失去制約。
主筆◎李偉?? 記者◎魏一平
化學的威脅
在沈曉寧的行李箱里,塞滿了各種型號的取樣瓶、防化服、膠鞋和口罩。日常的衣物只占了其中一個小小的角落,而且都是特別舊的衣服。因為她要去的地方,總是很臟、很臭,讓她感到特別惡心。
拖著這樣一個行李箱,這個文靜的女孩兒經常被安檢攔下來。傳送帶后面的監控器,對于箱子中紫色、黑色的小水瓶感到好奇。“幸虧,他們從沒讓我喝一口證明一下。要知道,那可是從排污口新鮮出爐的樣品啊,聞一下頭暈目眩,喝一口還不要了我的小命。”沈曉寧告訴本刊記者。她是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一名工作人員,在做污染調查的過程中,經常要去排污口采集樣品。
通常,清晨四五點鐘,沈曉寧和她的同事們就要開始工作了。在依稀可辨的晨光中,他們沿著江邊往排污口的方向走。空氣從清新,逐漸變得讓人無法呼吸,隨著刺激、酸臭的味道越發強烈,排污口就呈現在他們的眼前。
白天的取樣還是相對順利的。但是為了拿到污染的證據,還需要在不同時間段對污水排放進行“偵查”,從而找到異常情況。有點像警察經常干的工作——蹲點,從清晨到深夜,整整一天都需要不停地在排污口周圍巡邏。“難熬的是,在這樣氣味刺鼻的地方,守候一天可不是好玩的。”沈曉寧說。
晚上的工作更加重要。因為很多污染企業為了躲避檢查,都是在深夜偷偷將沒有處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。往往這時候,排污口的水量異常大,顏色很深,水面上全是白色的泡沫,延伸至江中間。“我不禁在想,他們究竟在排放什么東西!這次取20多瓶水樣大約花了白天兩倍的時間。將樣品運回去后,每個人都精疲力竭了。”沈曉寧說。
得到樣品,只是污染調查的第一步,然后他們會將樣品送到實驗室化驗,分析其中的有害成分與濃度,最后出具報告。其中很多化驗工作是在國外完成的。
近幾年來,綠色和平組織在中國展開了一系列環保調查。包括2010年“7·16”大連油罐爆炸與石油泄漏事故、珠江流域污染狀況、電子行業與紡織業排放調查。他們認為,工業化產生的化學污染,已經成為中國環境惡化的最重要敵人。
以水污染為例,按照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在2005年的報告,中國70%的江河湖泊被不同程度污染,其中50%的污染源來自工業。“而工業的污染后果,又遠比生活污染源嚴重得多。”綠色和平自身項目主任賴蕓告訴本刊記者,“這是因為工業領域使用和排放的化學品中,含有大量的重金屬和有毒的有機化學品。”這些有害化學品的危險性在于,他們不僅有持久性,不容易在環境中降解,而且還可以通過食物鏈在生物體內蓄積,產生更廣泛的威脅。
這些有害物質可以通過洋流、大氣沉降和食物鏈被送到遠方。因此在賴蕓看來,沒有人會幸免,“一些有害物質即使含量極少,也能干擾人類和野生動物的內分泌系統,而其他一些甚至具有致癌性或生殖毒性”。
綠色和平認為,化工業、電子產業和紡織業是這場化學污染的三大排放源頭。化工業生產了數萬種化學物質,電子行業使用了大量的鉛、鉻、汞等有害金屬,而紡織業則在印染環節中使用大量的化學助劑,產生大量的廢水,其中部分物質是有害的。
以化學原料業為例,在2009年環境統計年報中,占廢水排放量的14.2%,占化學需氧量的11.3%,氨氮排放量的35.7%,重金屬排放的11.6%。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建立了一個污染企業的數據庫,登記了自2003年以來涉及環境污染的5萬多家企業。其中以“化工”為關鍵字搜索可以得到6400多家企業,以“化”為關鍵字,則會增加到1萬多家。
化學工業是現代工業的基礎,也是生活得以運轉的基石。廚房里的燃氣、各種服裝面料、裝可樂的塑料瓶、洗發水、清潔劑與油漆……林林總總都是化工業的杰作。每年在全球實驗中,人類會制造出上千種新的物質。每年進入中國申報、登記、生產、銷售的化學物質達到100多種。
我國已生產和上市銷售的化學物質大約有4.5萬種,其中列入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危險化學品名錄的有3000多種。從某種意義上講,這4萬多種化學物質構成了我們身邊的世界。
2009年,賴蕓的同事馬天杰和張淼對《中國現有化學物質名錄2009》進行了一次比對分析。“我國當時僅有‘危險化學品名錄’,對于極毒、易爆、易腐和輻射性強的物質做了記錄。但是對于持久毒性、致畸致癌、生殖毒性、內分泌干擾物等化學物質,并沒有專門的名單和說明。”
于是他們參照了國際上一些優先控制的化學物質名單,對超過4.5萬種化學物質進行了梳理,識別其中的有毒有害嫌疑物質。用來比照的資料包括:《斯德哥爾摩公約》、奧斯陸-巴黎(OSPAR)公約的有限性動物之名單、美國環保署有毒物質排放清單中的PBT化學物質名單、歐盟高度關注物質名單等。
這項分析最終標注出了159種需要高度關注和控制的物質。在歐盟水框架指令的33種優先物質中有31個存在于中國現有化學名錄中。另外,美國有毒物質排放清單中的20種類優先于PBT物質中的11種類物質,以及歐盟REACH指令38種類高關注物質中22種類物質都存在于中國。這些物質中有很多都在紡織、電子、油漆和塑料等于生活緊密相關的行業中廣泛應用。
“比如壬基酚是一種內分泌干擾素,在我國紡織業中用于表面活性劑;而有機錫化合物被用于船的底漆,中國科學家的研究發現,中華鱘的消亡極可能和這一物質有關。”張淼告訴本刊記者。
盡管節能減排已經作為國家目標,環保部門的執法力度越來越強。但賴蕓對于化學污染的憂慮絲毫沒有減輕。“監管機構根據化學耗氧量(COD)和生物耗氧量(BOD)來評定企業的排污標準。但這是針對常規污染的方法。問題是,有毒有害物質被人為制造和使用,它們并不能在污水處理廠中被消解掉,最終還是進入到環境中循環。”
產業大遷移
PTA(精對苯二甲酸)是一種重要的化學原料,主要用于生產聚酯。而聚酯纖維(滌綸)是合成纖維最主要的品種,在世界合成纖維總產量中占將近80%的比例。瓶級聚酯切片則用來生產礦泉水瓶和碳酸汽水瓶。生產PTA則需要上游產品PX(對二甲苯)。石油經過一定的工藝過程生產出石腦油(別名輕汽油),石腦油再經過一定工藝過程就可以提煉出PX。
如果不是廈門與大連PX項目的爭議,“對二甲苯”不過是一個冷僻的專業名詞。2002年以前,我國限制對PTA的投資,因此上游PX的需求增長也相對平穩。2002年修訂的《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》將PTA由限制類改為鼓勵類,國內市場一直被抑制的需求迅速爆發,并直接拉動了上游PX的需求。
某種程度上,PX的消費與生產,直觀地體現我國這一輪化工業的狂飆速度。
2003年,我國PX進口突破100萬噸,2008年達到340萬噸,成為世界最大的PX消費國與進口國。在巨大的需求推動下,PX項目投資備受追捧,一大批新項目陸續上馬,生產能力迅速放大。“十一五”期間,國家發改委批準的新建PX項目共有6個,分別位于遼寧、江蘇、福建和廣東,2009年產量達到600萬噸,2010年達到747萬噸,產能居世界首位。中國產量已經占到了全球產量的近1/4。
2000年后,中國進入了新一輪重化工業時期。化工業的增長始終維持著GDP增速的兩倍。石油和化學工業規劃院總工程師李君發告訴本刊記者,近10年石化業總資產年均增速在15%以上,利潤年均增速18%以上,產值、固定資產投資及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速20%以上。
2010年我國石化業總產值為8.88萬億元,僅次于美國,居世界第二位,其中化學工業產值居世界第一位。按照國際和國內發展規律,石油和化學工業發展速度一般高于國民經濟發展速度,“十二五”期間仍將將保持10%左右的增長速度。按照李君發估計,2015年石化產業的產值會達到15萬億元左右。
除了因環保而受關注PX產量已達世界第一,化肥、農藥、染料、純堿、燒堿、甲醇、輪胎產量也居世界第一。原油加工量,及重要的基礎化學產品如乙烯、合成樹脂、合成橡膠的產量居世界第二位。如果從化學產品的生產能力看,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化學工業國。
按照國際規律,大型石化產業沿大江、海岸分布,一方面方便大宗貨物運輸,解決生產用水需求;另一方面則利用江海的龐大的容納力,方便排污。我國也不例外,從2003年開始,我國重化工業布局在沿海地區已經成普遍趨勢,各地重化工業比重占規模以上工業的70%左右。從北向南1.8萬公里海岸線上,大碼頭、大化工在許多省市到處落腳。在中國八大石化產業基地中,除了黑-吉基地和西北基地外,其余六大基地都分布在東部海邊和長江沿岸。其中大連憑借港口和政策優勢,已經取代大慶和吉林,成為目前中國最大的原油加工基地。
按照德意志銀行的分析,中國2005年GDP占全球的12%,2015年將占到21%。由于人均化學品的消費與GDP有明顯關聯,即隨著GDP的不斷上升,化工產業在中國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上升。
另一方面,中國化工業的發展與全國石化公司的產業轉移同步。與其他制造業一樣,在過去的10年間,跨國公司石化巨頭都已在中國建立了巨大的生產基地。德意志銀行的報告進一步認為,2008年后的金融危機將進一步加快這種產業轉移的速度。2007年中國化工市場占全球11%,德意志銀行認為到2013年這個比例將飆升到19%~20%。
美國福陸工程公司亞洲業務高級副總裁喬德哈瑞認為,在中國建石化工程優勢明顯。“從我們已經獲取的數據看,中國正在規劃或者建設的項目數量已居世界第一,我們公司在歐洲已感覺到項目數量下滑的威脅。另一方面,在中國進行石化項目工程建設存在很大的成本優勢。根據我們的保守估計,如果在美國做一個項目成本是100,那么在中東的成本就是110,而如果在中國建設的話,成本就是80甚至更低。”喬德哈瑞說。
地方政府成為石化項目最初鑒定的擁護者和最實際的受惠者。由于石化產業鏈長,不同化工產品互為原材料,產業的聚集度極高。一家煉油、乙烯企業落戶后,將帶動數家相關化工企業建廠。無論對投資規模、GDP、就業、財政收入都是極大的拉動。
作為石油化工的“龍頭”,乙烯是合成塑料、合成纖維、合成橡膠、醫藥、染料、農藥、化工新材料和日用化工產品的基本原料,也是用途最廣的基本有機化工原料。目前一家百萬噸級的乙烯企業至少需要500億元的投資,而帶動的相關產業投資則會超過1000億元。
歡迎發表評論我要評論
上一頁 1 2 下一頁
?????新浪獨家稿件聲明:該作品(文字、圖片、圖表及音視頻)特供新浪使用,未經授權,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載。